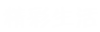(四)《禀母》函7通谈及与太平军作战漏洞百出
1.史实错乱,“署”“授”混淆
第37函《禀母》写道:“前贼犯上海,上海官绅立会防局……至是贼犯吴淞口,又盘踞浦东高桥镇……旋华尔阵亡,白齐文索饷不遂,投贼军,于是以戈登代领常胜军。二月,曾夫子遣男赴上海……皇恩浩荡,授男江苏巡抚……遂于十二日拜表谢恩,受职视事。而别授薛焕通商大臣,专办交涉事宜。”早在抗战前夕,“上海通社”社员撰写《近代名人在上海·李鸿章》时,此信被全文征引〔23〕。家信不厌其说地历述两年间的军政要事有悖常情,而且叙事时序颠倒,因果错乱。事实上,白齐文索饷是1863年1月,索饷不成被免职, 洋枪队统领由奥伦暂代,3月25日由戈登正式充任〔24〕。8月初,白齐文投奔太平军。此函把白齐文投奔太平军说成是戈登接任的原因,显然是颠倒因果。再者,李鸿章抵达上海是1862年4月8日,而上述事件以及华尔于1862年9 月在慈溪战死,都是李抵沪一年多后发生的。此函将上述各事作为李到上海的背景或前提,显然不合乎事实。另外,1862年4月15日, 清廷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,薛焕改充通商大臣,5月13日李接受抚篆〔25〕。同年12月3日(十月十二日),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〔26〕。因此, 李“署”苏抚与薛改任是同时,而李“授”苏抚是在薛改任的7个半月之后。清代官职的“署”与“授”有明显区别,李在接到“署”、“授”的谕旨后曾分别“具折恭谢”。此信以“署”为“授”,又含混地说“十二日拜表谢恩”,显然是编造。
2.颠倒事实,虚构“玉侄”
第39函《禀母》写道:“前日一役……法提督卜罗德亦阵亡。卒赖天佑圣朝,将士饮血,士卒用命,而贼众尽数覆没。现拟用士卒之余勇,进援苏常,使贼腹背受敌,早日翦灭。”史实是, 李鸿章会同洋兵于1862年5月17日攻占奉贤南桥镇后, 并未确定“进援苏常”的作战路线。清廷当时的战略意图很重视镇江,李鸿章赴上海前半个月,曾国藩曾计划派李鸿章率部“濒江而下,傍贼垒冲过,以援镇江”〔27〕。3 月28日上海官绅雇洋轮七号抵安庆后,李才最后决定进驻上海。李部到上海后,“屡奉移驻镇江之旨”〔28〕。甚至在南桥之战一个多月后,李鸿章在《权衡沪镇缓急片》中,仍不得不提出“容臣将沪事办妥即移师出江”的许诺与请求〔29〕。显然,此函“进援苏常”之说是将后事推前了。
第41函《禀母》写道:“前日圣旨下,命薛焕调京使用,着男暂署办理通商事务……三弟在署,读书写字,一如往昔办理琐事,实获儿心。季弟与文儿、玉侄耕读之道,不知可慰先人于地下否?”此信内容也出于编造。清廷命薛焕调京是1862年5月5日(四月九日),此信称“前日”,当为5月7日所写。而其时,李鹤章还未到上海。据记载,李鸿章率淮军赴沪时,李鹤章所统亲兵一营和各营马匹,“洋船不能尽载”,由李鹤章统带,“绕道皖北,押赴下游”,“由海门渡上海”〔30〕。6月3日,即谕令薛焕调京后一个月,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中说:“三舍弟已带马及勇,至仙女庙,望前可抵沪。”〔31〕“望前”即五月十五日(6月11日)才可抵沪,岂能在5月初“在署读书”。再者,根据第67函《致瀚章兄》行文,“玉侄”意指李瀚章之子。但据记载,在1862年前,李瀚章只有长子李经畲一个儿子,此时年方四岁,谈不上“耕读”,而且不名“玉”。事实是,1862年李瀚章从湖南去广东做官,幼儿李经畲随父母同往,并未与祖母在一起。因此,“玉侄”如同前文考辨的“文儿”一样,也是虚构的。
- 丹驹|FGO角色名字大改,都按照历史知识命名,没有偏离原型设定
- 少林功夫|张大仙新的定妆照才拍1个月,就派上用场了,这次与少林功夫有关
- 焰尾|按照模板来看的话,野鬃算是风笛的下位,但是她又更像是一个摔炮
- deck|索尼前任总裁晒《地平线:零之曙光》Steam Deck照片
- 玩法|如何拍出最美仙侠照?get《梦幻新诛仙》最佳拍照姿势
- ps5|《死亡回归》2.0更新上线 追加暂停功能以及拍照模式
- 支付宝| 儿童用药可以直接按照成人 儿童用药蚂蚁庄园10.26答案
- 小米回应新手机出现陌生人照片详情介绍| 小米回应新手机出现陌生人照片详情介绍
- 玩家|日本游戏开发商开罗软件告玩家书 国内代理严重侵权
- 英雄联盟|LOL手游国服首位王者诞生,辅助玩家照样Carry全场